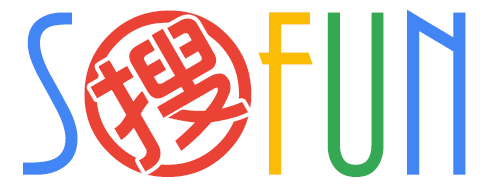華盛頓大學宣佈該校第四例新型冠狀病毒疑似病例排除,兩位教授——一位公共政策教授和一位公共衛生教授——隨即邀請學生和教員們參加了一場小型晚宴。和校內其他地方乃至世界各地一樣,在宴會上,冠狀病毒成了唯一的話題。但是,其中一位參與者,一名公共衛生學生,表示她受夠了。盛怒之下,她一口氣說出一組統計數據。
該病毒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導致1100人死亡,在美國大約感染了十幾人。令人擔憂但要常見許多的流感每年造成約4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上個流感季的死亡的34200美國人和之前一年流感季死亡的61099個美國人。

新型冠狀病毒的死亡率目前還很難說,根據估計,其最高值可達流感的20倍,但如果除去被疫情沖垮的中國湖北省,某些估計值低至0.16%。與流感差不多。
學生問,公衆反應存在如此極端的反差,不覺得奇怪嗎?
晚宴的合辦人、公共政策教授安·博斯特羅姆(Ann Bostrom)在回述當晚的情形時笑了起來。作爲一名人類風險評估心理學方面的專家,博斯特羅姆說,這位學生對病毒的理解是正確的,但對人的理解卻不正確。

她說,公共衛生指標可能會根據絕對的致死率將流感與新型冠狀病毒並列,甚至排在新型冠狀病毒前面,但人自有一套衡量危險的方法。而被命名爲COVID-19的新型冠狀病毒病幾乎擊中了我們所有觸發認知的因素。
這解釋了全球範圍內的焦慮情緒。
當然,對席捲中國乃至其他地方的冠狀病毒疫情暴發感到恐懼,絕非不理智的表現。

但是心理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說,從人們對這種病毒近乎恐慌、而不把流感這種嚴重的威脅當回事的現象中,我們可以得到一條教訓。它說明了人們在風險評估中的無意識偏見,以及常常以衝動來引導我們的迴應方式——有時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我們的大腦如何評估威脅

專家曾經認爲,人們會像精算師那樣評估風險,當正在變道的汽車離得太近,或當本地犯罪率激增的時候,就會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然而1980年代的一系列心理學實驗顛覆了這種想法。
研究人員發現,人們使用一系列思維捷徑來衡量危險。這往往是無意識的,意味着本能發揮的作用可能比他們意識到的要大得多。
世界充滿着大大小小的風險。理想情況下,這些思維捷徑可以幫助人們找出哪些問題值得關注,哪些需要忽略。但是它們可能並不完美。

冠狀病毒也許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現代風險心理學的先鋒、俄勒岡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說:“導致人們提高風險感知的按鈕,這一次全部觸擊到了。”
當你遇到潛在風險時,你的大腦會將它在過去的經驗中進行一次快速搜索。如果它可以輕易地喚起多個令人擔憂的記憶,那麼你的大腦就會作出危險很高的結論。但是,它常常無法評估這些記憶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墜機。

如果兩次墜機事件連續發生,坐飛機突然變成了可怕的事情——即使你的意識頭腦知道那些墜機事件是極小的機率,對你下一次的飛行幾乎沒有安全影響。但是,如果你隨後坐了幾次飛機都沒有任何問題,那麼你的大腦很可能會開始告訴你坐飛機是安全的。
斯洛維奇說,涉及冠狀病毒時,好像人們正在經歷一個又一個飛機墜毀的報告。
“我們聽到的消息是死亡人數,”他說。“而不是98%左右的人正在從中康復,並且可能只患了輕症。”

這種趨勢也可以走向另一個極端,除了不必要的擔憂外也會導致不必要的自大。儘管流感每年導致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死亡,但大多數流感患者的感受平淡無奇。
研究發現,告知流感有多麼危險並不會改變這個情形。大腦的風險評估法直接蓋過了理性計算——這讓試圖提高流感疫苗接種率的衛生官員感到無盡驚愕。
“我們受到經驗的條件反射,”斯洛維奇說。“但是經驗會誤導我們對事物過於習慣。”
偏見,捷徑和直覺

人們對冠狀病毒風險的評估還涉及其他心理捷徑。
其中一個涉及新穎性:我們習慣於將精力集中在新的威脅上,尋找任何引發擔憂的原因。這可能導致我們沉迷於最糟糕的消息和最壞的情況,使危險看上去更大。
也許最強大的捷徑是情緒。

評估冠狀病毒帶構成的危險極其困難;即使是科學家也不確定。但是,我們的大腦似乎用一種更容易的方式:將情緒直覺反應轉化爲我們自以爲合理的結論,即使它與堅實的數據相悖。
“我們頭腦中的世界並非現實的精確複製品,”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2011年的書中寫道。“我們面前的信息的普遍性和情感強度,會左右我們對事件發生頻率的判斷。”
博斯特羅姆說,在極端情況下,這可能導致“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因爲我們的情緒衝動壓倒了我們的認知能力。冠狀病毒觸擊到了這些誘發因素,力度通常很強。

其中一個是恐懼。
如果一個風險看起來特別痛苦或令人不安,人們往往會提高這種風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機率的估計。關於冠狀病毒的報道通常帶有令人不安的圖像:不衛生的食品市場,整座城市的封鎖和人滿爲患的醫院。
另一個觸發因素是人們尚未完全瞭解病毒的威脅。它越不爲人所知,就會有越多的人擔心它,並高估它的威脅。
令人感到失控的威脅,例如失控的疾病暴發,會引發類似的反應,導致人們尋求重新實施控制,例如囤積物資。

我們自願承擔的風險或至少感到自願的風險,通常被認爲是低於實際風險的。一項研究發現,如果人們把危險視爲一個選擇,那麼危險會增加一千倍。
如果這個數字聽起來很高,那麼想想開車,這種危險絕大多數是自願承擔的,每年會導致4萬多美國人喪生。但是恐怖主義是一種我們被迫面臨的威脅,造成的死亡人數不到100。
有無數合理的原因使恐怖主義比交通死亡更能引起人們的強烈反響。同樣,快速傳播且人們知之甚少的病毒暴發相對於熟悉的流感也是如此。
心理學家說,這正是重點。
“所有這些事情都影響着我們的感覺,”斯洛維奇說。“這就是我們經受威脅的表現。不是風險的統計,而是風險的感覺。”
做出選擇

所有這些情緒都可以產生現實後果。
參考人們對1979年賓夕法尼亞州三英里島核電站部分熔燬的反應。雖然該事件沒有造成死亡,但它導致公衆要求從核電轉向化石燃料,而後者被認爲單單是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就導致了每年超過數千人過早死亡。
這種計算使老派經濟學家感到困惑,他們認爲這是非理性的。一位傑出的核電專家稱其爲“瘋狂”。
但這也有助於建立人們如何衡量風險的新心理模型。

斯洛維奇說:“我們的感覺並不太會做算術。”
在判斷低概率、高風險威脅,例如核戰爭、恐怖主義,或死於冠狀病毒或流感時,尤其如此。
斯洛維奇說,我們的頭腦要不就是傾向於將概率“基本上舍入爲零”,繼而反應不夠,要不就是專注於最糟糕。